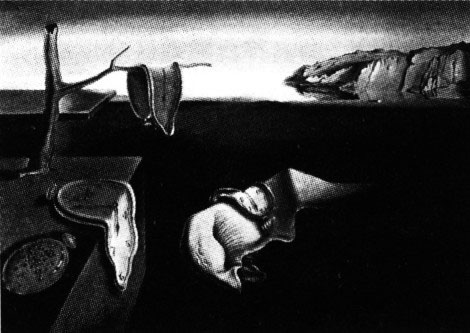《论生命》原文_什么意思_赏析
论生命
[英]雪莱
无论我们将自身的存在与感受称作什么,生命与世界总是令人惊叹的神物。对万物的熟视无睹,宛如一层薄雾,遮蔽了生命中的奇观,使我们不能窥见它的光彩。我们对生命的一些转瞬即逝的变幻景象赞叹不已,殊不知生命本身才是伟大的奇迹。帝国的盛衰更迭,王朝的土崩瓦解,以及扶持帝国王朝的高见宏论,同生命相比,何者为重?宗教团体和政治制度的生生灭灭,同生命相比,何者为重?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旋转,连同构成它的种种要素的运作,同生命相比,算得了什么?宇宙中的日月星辰——我们居住的地球便是其中之一——连同它们的运转与归宿,同生命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对于生命这一伟大的奇迹,我们并不惊讶赞叹,这是因为它显得如此超凡而又神奇。幸好我们对了如指掌且又莫测高深的事物熟视无睹,这层薄雾遮挡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免生惊异。否则,由于窥见神奇而产生的惊异,一定会威慑住引起惊异的客体,使之不能自如运作。
设若太阳、恒星和行星等天体尚未在宇宙间存在过,此时有一位艺术家,我不是说他已经大功告成,而是说他仅在脑海中构想出这些天体,继而用词语或在画布上给我们描绘出如今夜间苍穹赐予的美妙景象,然后用天文学的智慧阐明这一景象的来龙去脉,那么,我们定会对他推崇备至。或者,设若地球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景致:崇山峻岭、江河海洋、草木花卉,森林里千姿百态、如亭如盖的叶片,日出日落时的五彩缤纷,大气层中或浑浊或清明的种种色彩;如果有一位艺术家,运用他非凡的想象力,一一描绘出这些事物,那么我们的的确确会惊讶不已。倘若用“无人配获得创造者的称号,惟有上帝与诗人”这句话来赞美他,这绝对不是虚妄的吹捧。可是如今呢?人们对这些事物见惯不惊。兴味盎然地领略这些事物,便被认为是志趣高雅、卓尔不凡之人的突出标志。芸芸众生对这些事物是漠不关心的。这就是生命的特征:它包罗万象。
什么是生命呢?无论意志参与与否,我们的种种情思都会在脑海中涌现,于是我们便运用词语来表达它们。我们降临到世间,可是出生的情景无法记起。我们对婴孩时期的记忆,也只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残片。我们继续生活着,然而在生活中,我们丧失了领悟生命的能力。如果认为凭借词语便能洞悉生命的奥秘,这是何等狂妄自大啊!不过,词语若是运用得当,便可以昭示我们对自身的茫然无知,虽然仅此而已,也算非同小可了。我们无法回答的是;我们为了什么而生存?我们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出生是不是我们生命的开端,死亡是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结?出生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
逻辑最缜密精妙的抽象概念,给我们展示出一幅壮观的生命画面。虽然领悟这幅画面会令人惊心动魄,但它实际上却是由于我们对一再重演的生命组合习以为常而被湮灭的那番景象。因此,可以说,逻辑学为我们除掉了遮蔽这番景象的屏障。一些哲学家宣称,只有被感知的事物才是存在的。许多人对他们的论断深表赞同。我承认,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固有的各种信念与这一论断背道而驰,全都千方百计地予以抗击。我们必然是早有定论才会坚决相信:囊括外在事物的实实在在的宇宙,只不过是“梦一般虚幻的东西”。通俗哲学关于意识与物质承担那些观点,有许多荒谬绝伦、耸人听闻之处,在道德观念上也造成了许多致命的后果,在万物起源问题上又表现出极端的教条主义。通俗哲学的这一切缺陷,早已是我转向了唯物论。这种唯物论对于年轻肤浅的心灵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体系。它允许信徒们畅所欲言,并准许他们不作思考。但我不满意它对事物所持的观点。在我看来,人是一种抱负远大的存在,他“远眺往昔,瞻望未来”,他的“思想徜徉于永恒之中”,与稍纵即逝、腐朽衰败断然绝缘。他无法想象万物会毁灭;他只在往昔与未来中生存。他不展现他如今拥有的风貌,只展现他曾经拥有的风貌,以及将来应拥有的风貌。无论他最终真正的归宿是什么,他心中永远有一个精灵、与虚无缥缈、分崩离析为敌。这是一切生命、一切存在的特征。每一个生命与存在,既是圆心,同时又是圆周;既是万物所指向的点,又是万物被含纳的线。诸如此类的冥想,是唯物论与通俗哲学的意识观和物质观所不容的;它只与理智体系共存。
冗长地重述已为爱好探索的头脑所熟知的观点,不免显得荒唐可笑。只有专门从事深奥论题研究的著者才配对他们发表长篇演讲。也许,在威廉·德拉蒙特的《学术问题》中,我们可以找到对理智体系所作的最清晰有力的论述。经过他的一番阐释,倘若再用其他的词语转译他的观点,就显得徒劳无益了。原作一经转译,生动贴切之处遂荡然无存。即便一个论点一个论点地、一字一句地审视原著的整个推理过程,最有识别能力的英才也未能找出他的思路有何不清晰,致使他的推理并非必然导向他所得出的结论。
理智体系得到认可之后,结果如何?理智体系并没有确立新的真理,它对人的隐秘天性本身或其外在表现也没有提出新的真知灼见。它也许迫不及待地要创立一种哲学,但作为千秋万代的先驱,哲学任重而道远。理智体系朝着这一目标迈了一步,致力于消除谬误及其根源。它留下一道空白,一道往往理应由政治、伦理问题的改革者留下的空白。它让人的意识享受这道空白赐予的自由。倘若人们不曾误用言语与符号这些人的意识本身所创造的工具,那么意识便会在这种自由里尽情发挥作用。我这里所讲的符号,可作广义理解。它既包括这一术语的本来意义,也涵盖我所特指的意思。在这层特指的意思中,几乎所有熟悉的客体都是符号,这些符号并不指代客体本身,而是指代其他的事物,能够使人联想到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又引发出一连串的思想。由此说来,我们整个人生是一场关于谬误的教育。
我们姑且回忆一下童年时对事物的感受吧。那个时候,我们对世界与自身的理解是何等独特、何等热切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那时在我们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可如今却不再是举足轻重的了。但我并不执意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一番比较。我们当年并不像如今这样,习惯性地把我们的见闻感受统统与我们自身区分开来。它们那时似乎要融为一体。从这一点来说,有些人永远是孩子。他们极易沉湎与所谓梦幻的状态之中,感到他们的天性仿佛融进了周围的宇宙,或者周围的宇宙仿佛与他们自身浑然一体,于是物我两忘,不觉丝毫差异。这种状态常常出现在人们对人生有极其热切活跃的理解之前、之中或之后。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这种能力通常渐渐衰退,他们也就变成机械性的、习惯性的行事者。因此,感情与推理便演变成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思想与一连串因一再重复而形成的所谓印象相结合的产物。
理智主义哲学最精密的演绎所展示的人生观是万物统一。世间只存在着被感知的事物。人们用“观念”与“外在客体”的名称浅陋地区分思维的两种类型,而这两种思维类型之间的差别确乎有名无实。依照这一推理思路,我们还可以发现,截然不同的个体意识的存在同样是一种幻觉,虽然它与我们现在用来审视其本性的东西相类似。“我”、“你”、“他们”这些词语,并不是表示存在于上述思想集合体之间的实际区别的符号,仅仅是用来指代同一心灵的不同变体的标记。
但是,请不要误以为这一见解会导向这样一个极其荒谬的推论:我,这个正在写作、思考的人,就是那个心灵;我只是它的一部分。“我”、“你”、“他们”这些词语,不过是为了便于归类而创设的语法手段,丝毫不带通常附属于它们的那种严密、专有的意义。要找到合适的术语来表达理智主义哲学传递给我们的如此微妙的概念,绝非易事。词语几乎不再为我们所用。因此,假如我们在俯视自身孤陋寡闻的黑暗深渊时变得头晕目眩,那委实不足为奇。
事物之间的关系依然如故,不因任何思想体系而有丝毫改变。事物一词可以理解为思想的任何客体,即任何一种以独特的理解力对之进行考究的思想。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变,构成我们知识的原材料。
生命的原因是什么?即是说,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哪些与生命性质不同的力量曾作用于或正作用于生命?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千秋百代一直在疲惫不堪地忙着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其结果为——宗教使然。然而,万物的基础不可能是通俗哲学所宣称的意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对意识的属性有过一番切实体验,我们便会知道意识不能创造事物,它只能感知事物。倘若逾越对意识属性的切实体验,一切论证是何等徒劳无益!有人说,意识也是人生的原因。但“原因”一词之表示涉及人们如何理解两种思想相互关联时人类意识所处的某种状态。倘若有人想知道通俗哲学在解答这一重大问题时有多么力不从心,那么他们只需不带偏见地回想一下自己头脑中种种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就可一清二楚。意识的原因,即存在的原因,断不可能与意识本身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