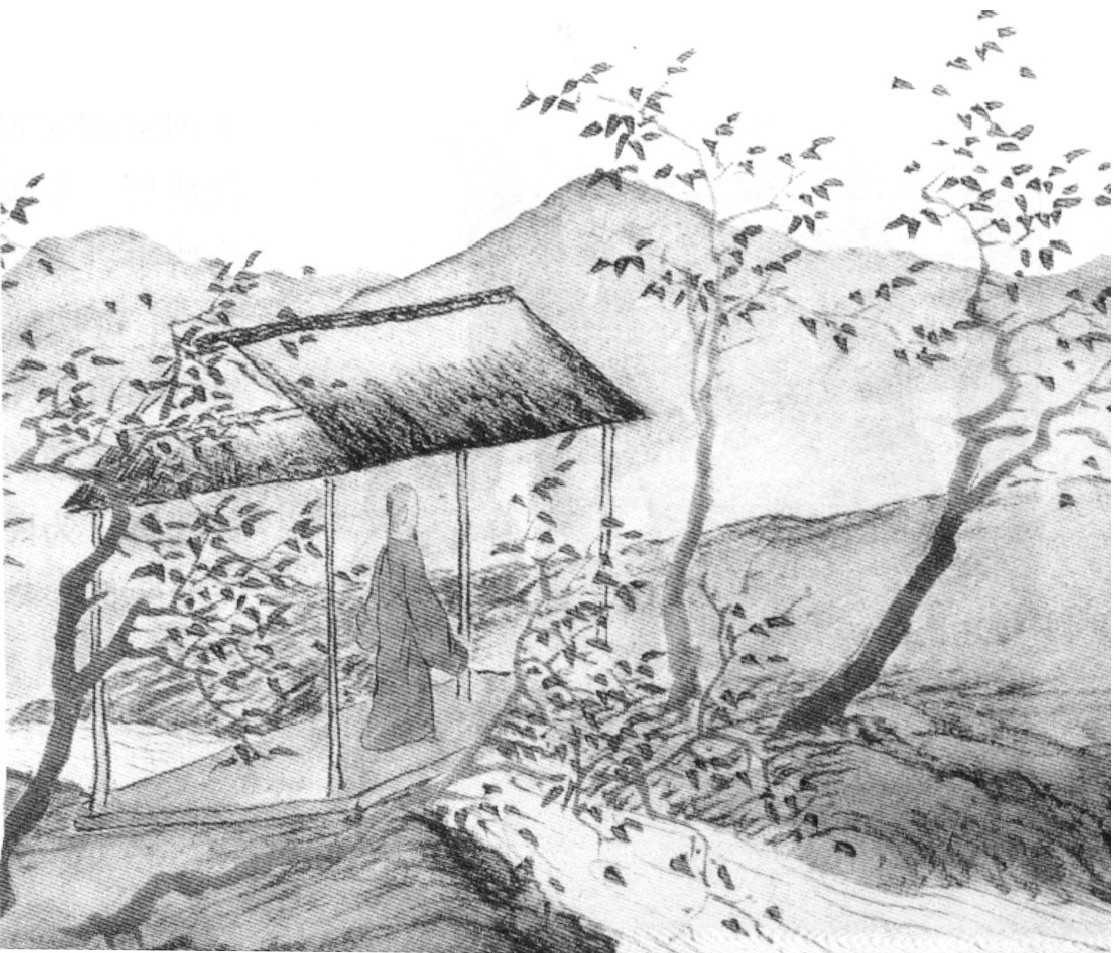杨万里:今日诗坛谁是主
杨万里:今日诗坛谁是主
一
不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首当数谁家,可以肯定的是,范成大绝对是四人中人缘最好的一个。
范成大晚年自号石湖居士,将自己的诗文编成《石湖集》,请好友杨万里作序。杨万里性情狂傲,却独独对范成大推崇备至,曾道“一生狂杀老犹狂,只炷先生一瓣香”。他在序言中不吝溢美之词,称赞范成大“今海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这是把范成大放在南宋“中兴四大诗人”行首了。
陆游对范成大亦是十分敬重,于范成大病逝时曾挽诗悼之:“孤拙知心少,平生仅数公。凋零遂无几,迟暮与谁同!……”数日后,又因梦见范成大,再次题诗:“速死从公尚何撼,眼中宁复见此杰?”恨不得追随范成大一起死。
但是反观陆游对杨万里怎样呢?
这从陆游的《送子龙赴吉州掾》长诗中就可窥一斑了。这首诗作于陆游的二儿子陆子龙去吉州为官之际,陆游为子送行时叮嘱了一系列赴任注意事项,甚至包括如果遇到杨万里该怎么办:“又若杨诚斋,清介世莫比。一闻俗人言,三日归洗耳。汝但问起居,余事勿挂齿……”
这说的是杨万里为人高冷,听到不顺耳的话就会像上古隐士许由那样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而且要连洗三天表示鄙视。陆游叮嘱儿子:你见了他只管执晚辈礼,问候健康就好,别的话就一句也不要多说了,免得招人烦。
从诗中可见,陆游对杨万里虽然尊重,却不亲近,不过点头之交而已。不过陆游对人一向客气,即使是面对并不亲近的杨万里也是充满赞颂之辞:“诚斋老子主诗盟,片言许可天下服。”“文章有定价,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心甘情愿承认自己不如杨万里。
姜特立亦有诗称:“今日诗坛谁是主,诚斋诗律正施行。”项安世则说“四海诚斋独霸诗”,皆以杨万里为当时之冠。
而杨万里自己也颇以诗才自豪。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回忆,自己少年时曾随父亲拜访杨万里,正值杨万里刚写完一首咏月诗,诗末云:“焉知万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团月。”看到罗家父子进来,杨万里非常得意地把诗作拿给他们看,并且说:“老夫此作,自谓仿佛李太白。”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和张孝祥、虞允文是同榜进士,中举后得职赣州司户,不久调任永州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区)县丞,比北宋的黄庭坚还可怜。因为黄庭坚任职的叶县到底是中原腹地,而永州却是自古以来放逐官员的穷乡僻壤,唐朝时柳宗元就是在这里写下《永州八记》的,“永州之野产异蛇”,乃是瘴疠蛇鼠之地,杨万里等于刚做官就被贬了。
不过就因为在永州做官,杨万里才有机会“一日而并得二师”,也就是同为秦桧所贬的张浚和胡铨。
张浚是因为高喊主战被秦桧贬到永州来的,郁闷得闭门谢客,像杨万里这种后生小子原本是不放在眼里的。可是禁不住杨万里一再登门,又托其子张栻致意,精诚所至,终得张门为开。张浚见了杨万里,倒觉得这小子很对脾气,与之甚契,并勉励其“正心诚意”。
杨万里因此把自己的书室名之为“诚斋”,还请胡铨为他写了《诚斋记》,终生以两位爱国名臣为效仿的榜样。
特别的是,《宋史·张孝祥传》提及高宗殿试,曾谕宰相曰:“张栻、孝祥词翰俱美。”
莫非张栻也是这一年的进士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他也该在群星榜中,成为杨万里的同年,两人相交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可惜《宋史·张栻传》里却只说他“以荫补官”,得孝宗赏识,“遂定君臣之契”。似乎并未参加科举,亦未有高宗面试。
不过,即便两人不是同学,亦是同道中人,便连诗风也是相似的。张栻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一首绝句:
立春偶成
律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
而杨万里最为我们熟悉的诗莫过于那首西湖荷花: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杨万里一生以张浚为师,张浚远征前特地举荐杨万里为临安府教授,可惜杨万里未及赴任,就因父丧报了丁忧。
乾道三年(1167)春,杨万里服满复职,前往临安,谒见同年登科、如今已做了枢密使的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分为《治原》《人才》《民政》等三十篇,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
科举同年素有弟兄之义,是仕途中最重要的人脉资源。况且虞允文知人善用,对杨万里自然格外看顾,遂举荐其为国子博士,自此杨万里开始在京任职,颇受重用。
二
杨万里为人刚直,素有清名。淳熙十二年(1185)东宫缺少讲学,孝宗亲自提拔杨万里为太子侍读。东宫官僚都以得到一个正直的人而奔走庆贺,太子也对他很敬重。
有一次宰相王淮问他:“宰相最先办的应是什么事情?”杨万里很具远瞻性地回答:“十二世纪最缺乏的是人才。”王淮又问:“以您之见,以为哪些才是人才呢?”杨万里便推荐了朱熹等数十人,后来一一得到重用。
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驾崩,孝宗不愧这个“孝”字,竟想依照臣子惯例三年守丧,让太子赵惇监国。
这其实也是符合儒家精神的。《论语·宪问》中说,子张问孔子:“《尚书》记载,‘高宗谅阴,三年不言’,该怎么理解?”孔子说:“岂止是殷高宗呢?古人都是这样的。先君死了,君主三年不问政事,大臣各司其职,听从宰相领导。”
国家机器真正上了轨道,每个齿轮都能运转自如,那个最高领导谋不谋事都不重要了,是宰相领导还是太子监国,都可以照样运转。
孝宗朝虽然偏安江南,却是南宋发展最好的时期,加上孝宗至孝,会有这种想法也不稀奇。并且,将国政交给太子监理而非正式传位,也便于考察太子的治国能力,倒也不算坏事。
倘若当时真这样做了,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赵惇正式即位后日渐昏聩,在位仅五年就被太后强行废掉的惨祸了。
不过皇帝居丧三年毕竟是大事,群臣俱上书力谏。杨万里也在私下叮嘱赵惇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太子贸然答应,倘或他日帝心生疑,怪责太子觊觎帝位,父子生隙,悔之莫及。与其将来出事不能转圜,不如干脆辞谢不居位。愿殿下再三推辞,且莫居位。”太子果然听从。
然而在讨论配享高宗的大臣名单时,杨万里为了争取张浚得此殊荣,与翰林学士洪迈争执不下,遂指斥洪迈专辄独断,无异于“指鹿为马”。
他骂得痛快,却忘了忌讳,打老鼠伤玉瓶儿,把当今皇上也一起骂进去了。这典故说的是秦二世时,宰相赵高位高权重,一手遮天。有一天他为了测试群臣对自己的依附态度,故意驾着一头鹿随从二世胡亥出行,胡亥问他:“丞相为什么驾着一头鹿呢?”赵高说:“陛下看错了,这是一匹马。”
秦二世诧异:“明明是鹿呀。”赵高说:“陛下要是不信,可以问一问群臣。”说着转向众臣:“明明我乘的是一匹马,陛下却偏说是头鹿。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啊?”
众臣惧怕赵高权势,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故意迎合说是马,只有少数人说是鹿。在这种情况下,胡亥也不敢再坚持看法,只好承认赵高乘的是马。
在这个故事里,赵高固然可恶,胡亥却也是软弱无能之至。而且秦二世而亡,为君主大忌,杨万里这个典故引用得可说极为不当。因此孝宗怫然不悦:“洪卿若是指鹿为马,又将我视为何种君主?”遂将杨万里贬职。
杨万里一生以张浚为师,也因为张浚始得世人瞩目,如今又因为张浚而贬官。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洪迈,便是替辛弃疾新宅落成写《稼轩记》的那位。
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禅位,赵惇即位,史称宋光宗。然而登基没多久就得了精神病。
彼时杨万里官拜秘书监,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愧于没把学生教好,不久便主动请辞,挂冠还乡,从此隐居乡中十五年,再未出仕。
杨万里一生诗作两万多首,传世四千二百首,被誉为一代诗宗。其语言风格浅近明白、清新自然,被称为“诚斋体”,最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其中多首选入中小学生课本或辅助教材:
小 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宿新市徐公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闲居初夏午睡起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杨万里以诗成名,其词作又是另一种风格,擅以口语入词,情趣盎然。且看一首咏月之作:
好事近·七月十三日夜登万花川谷望月作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 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
三
光宗只做了五年皇帝便禅位于其子赵扩,史称宋宁宗。
和之前的孝宗一样,宁宗即位之初,一方面迫于主战呼声,另一方面也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显示自己是个有为君主,而最好的证明就是北伐,收复国土。
于是,以韩侂胄为首的主战派当权,一党独大,如日中天,并对主和派人物赵汝愚等发起了围攻。
赵汝愚为赵宋宗室,喜欢广揽名士,为自己扬名。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荐用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宁宗讲学。韩赵不和,赵汝愚被贬,朱熹便约集吏部侍郎彭龟年一起弹劾韩侂胄,结果被罢官。
在韩侂胄集团的策划下,宁宗下令禁止理学,定理学为伪学,又订立伪学逆党籍,禁止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担任官职,参加科举,是为“庆元党禁”。这是宋代言论管制非常严厉的一次事件。
朱熹是李侗的弟子,也就是程颢的四传弟子,至此完全走上了祖师爷的老路——同样做了帝师,同样插手党争,同样导致理学被禁。
但是禁止官员任事,并不能禁止民间议论。有人在城墙上贴了一首题壁诗,大骂韩侂胄愧对祖宗:“九原若见韩忠献,休说渠家末代孙。”末尾还堂而皇之署上自己的大名“敖器之”。
这首诗就和那首“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题壁诗一样风传江南,但是韩侂胄明知敖器之是太学里的学生,也没有把他怎么样,而且因其并不在党禁名单里,后来参加科举试,韩侂胄也仍然没有作梗,由着他考上了进士。
这份气度,足以甩那个因为陆游在解试中抢了孙子头名就干脆将其在省试中除名的秦桧几百条街了。
但是韩侂胄的大度,并不能让理学一派对其停止口诛笔伐,不但将他本人视为恨不得寝皮食骨的头号天敌,连带与韩侂胄交好的陆游也成了被嫉恨的对象,而作为杨万里的反衬成了负面人物。
但究其根底,仍是文人闲气的文章官司罢了。
原来,庆元三年(1197)春,韩侂胄得太皇太后赏赐南山别园,大兴土木,修筑南园,嘱托杨万里作记,并许以门下省高位。但是杨万里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官可弃,记不可作!”
韩侂胄遂转托陆游作记。
陆游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主战派,交游遍天下而一生不得志。如今当朝宰相求其写篇园记而已,又不是什么赞歌颂词,自然没有推托的必要。更何况韩侂胄主张收复失地兴兵抗金,这与陆游的一贯主张不谋而合。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何况只是写篇文章呢?写字,对陆游来说是倚马可待的事,所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南园记》。
不料,这竟然成了朱熹鄙薄陆游的理由,竟在文中公然讦击说:“(陆游)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
这番评价被收入了《宋史·陆游传》结尾,从此陆游就被打上了晚节不保依附权贵的烙印。其实陆游何罪之有呢?
朱熹身为当世大儒,宫中讲学,参与到党争已是不智,更何况还要联党弹劾重臣,说到底只是为了党同伐异。而他对陆游的这番评价盖棺论定,更有违圣人之道,仁人之德。韩侂胄又不是秦桧,朝廷的那些党争是非更与陆游无关,写篇文章而已,怎能成为晚节不保的罪证?
尤其朱熹和陆游也算旧识,对其一生为人十分了解,完全不应该有此误解。陆游为人正直,品行无污,平生无恶行,诗名更盛于世,朱熹不便对其全盘推翻,却攻其一点,含糊其词,这番话说得相当委婉而诛心。说到底,不过是因为嫉妒与迁怒罢了。
而且,理学一派打着孔孟之道的招牌,却丝毫没有温良忠恕的德行。输了被禁,固然恨气冲天,自视委屈;占了上风,便拨弄历史,颠倒黑白,对王安石污言相向,对韩侂胄掘墓鞭尸。这又有什么仁义可言呢?
而杨万里拒绝了韩侂胄,自然便得到了理学一派的吹捧,就连他晚年的隐居,也被理学后人说成是受到韩侂胄的排挤打压。其实杨万里早于光宗朝便谢病归乡,自此幽屏与世绝。韩侂胄称相是在数年后的事,向杨万里求赋纯为欣赏,并无党争目的,被拒绝后虽然不爽,也未见有打压之为。
甚至考虑当时背景,韩侂胄邀请杨万里撰文之举,非但不为打压,而恰恰相反,是含蓄地向理学政敌示好。因为此后不久,韩伉胄便解绑了理学党禁,呼吁一致对外,共同抗金复国。
倒是杨万里一直耿耿于怀,揪着曾经的恩怨不放。
为了显示北伐决心,宋宁宗于嘉泰四年(1204)追封岳飞为鄂王,两年后又削去秦桧爵位,给了投降派一个明显警示。彻底压制了主和的声音后,宁宗便在两年后任命宰相韩侂胄伐金,正式开战。
杨万里于病榻上得知韩侂胄轻率出兵,失声痛哭,唤人取纸笔来写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写了十四言留别妻子,写罢掷笔,一恸而绝。
时为开禧二年(1206),杨万里终年八十岁,死后追赠光禄大夫。
四
韩侂胄伐金在言论上的准备很充分,军事准备却不足。出兵前,宁宗解除了对伪学逆党的禁令,重新任用一些在籍的理学官员,争取他们一致对外。
但是从杨万里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理学人士对于韩侂胄的仇恨远超过对金兵,因此采取不合作态度,拒不听令。韩侂胄调遣多名将领,都遭到推辞,伐金将领乏人。更有内奸吴曦在四川私通金朝,图谋割据,导致韩侂胄左支右绌,内疲外乱。
宋军出兵伐金时,西线吴曦叛变,在金兵临江时按兵不动,任由金军东下。韩侂胄日夜盼望四川进兵,陆游也仗着蜀中相识的一点旧情多次致书催促,吴曦皆置之不理。金兵入城时,吴曦更是索性下令撤防。守军孤军不敌,金军陷关。
东线接连败退,领军的丘崈主和退守,宋军伐金部署遭到严重破坏,韩侂胄日益陷于孤立。
《宋史·郭靖传》中记载了一个与射雕大侠郭靖同名的四川豪绅,在吴曦降金后,因既不愿归顺金国,也不愿离乡远去,遂对兄弟说:“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竟赴嘉陵江而死。
而这种“宁为赵氏鬼,不弃汉衣冠”的想法,在南宋“崖山之战”后表现得尤为彻底。宋人风骨,可见一斑!
为了坚持北伐,开禧三年(1207)正月,韩侂胄自出家财二十万补助军需,联合杨巨源、李好义等诛杀吴曦,收复四川。可以说,不论结果成败,他的抗敌决心是坚定的,姿态也是磊落的,而北伐战争中也曾经取得了一些胜利。
之后,宋军一路收复西和州、成州、阶州(都在今甘肃)和凤州、大散关(都在今陕西),所向无敌,形势一片大好。
如果宋廷上下一心,借着这份斗志一鼓作气,是完全有可能就此北上伐金,完成复国大业的。
然而战果方显,宋军内部安丙、孙忠锐等人就因争功而彼此牵制,甚至互相设计暗杀,伐金刚刚取得的一点成绩,很快便被内讧给消耗净光了。
这时宁宗动摇了,并暗中派人与金国议和。金人对韩侂胄恨之入骨,提出的议和条件之一竟是索要韩侂胄的人头。韩侂胄闻之,怒而上书请求整兵再战。
此前宁宗立后时,韩侂胄曾持异议,因此杨皇后深恨之,此时便向宁宗大吹枕头风,说韩侂胄再启兵端,于国家不利。宁宗不理。杨皇后便索性密信指使投降派代表史弥远暗杀韩伉胄,事后才奏报给宁宗。
之后,投降派割下韩侂胄的头,用匣子装起来送往金国,签下了“嘉定和议”,也就是“函首安边”。投降派占取上风,完全接受了金朝提出的条件,完成了和议,这是宋金开战以来的第三次屈辱和议。
韩侂胄败了。
于是理学后人本着“成王败寇”的定论,将韩侂胄毫不留情地定义为“奸相”,是致使大宋国势衰弱的千古罪人,杨万里则成了反对奸佞的大智大贤之烈士。
其实韩侂胄一生并无昭彰恶迹,更为抗金报国而死,其污名完全是因为后世理学家占据话语权而来。
不妨设想,如果韩伉胄胜了呢?是不是就成了厥功至伟的民族英雄?
张浚主持的“隆兴北伐”只打了几十天就败了,杨万里仍然为其配享宗庙事争抢得死去活来;而韩侂胄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一年多,且打得互有胜负,宋金对峙,堪称岳飞之后抗金将帅中最具威胁力的名字,怎么就成奸臣了?金人收到韩侂胄的首级,还要礼葬于其祖先韩琦墓旁,评价他一句“忠于其国”呢,宋人怎么反倒对其口诛笔伐?
朱熹以杨万里反对韩侂胄而盛赞其气节,却以陆游为韩写《南园记》批评其晚节不保。似乎谁是韩侂胄的敌人,谁就是义士,反之则为奸佞。
可是比道学先生们更恨韩侂胄的乃是金国,甚至非要见到韩侂胄的人头才肯议和。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金国当然是大宋的敌人,那么金国最仇恨的韩侂胄是否就应该是大宋的忠臣呢?
陆游因为主战而与韩侂胄投辖,又有何污之有?倒是朱熹如金人般视韩侂胄为仇雠,其根源不过是为了书生意气,其立场又当如何视之?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国难当头,山河破碎,臣民应当主战抑或主和?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北宋的寇准。辽人来袭时,有大臣建议真宗出宫避祸,而寇准孤注一掷,力劝真宗亲临前线,鼓励三军,赢得澶州大捷。而在北宋得胜的前提下,又是寇准促成真宗与辽国签下“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百年安宁。
之后数代宋主都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意,却因为时机不成熟,一直未有所动。直到徽宗时,才偏信奸宦童贯之言,妄举发兵,联金伐辽,结果授人以柄,灭了辽国,也把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金国的枪眼下。
所以,真正的名臣不在于主战还是主和,而在于清醒地相时而动,和平时代未雨绸缪,国难来时悉心部署,赤胆报国。
像李纲、宗泽誓死守护东京,自然是忠臣良将;而投降派却在此时怂恿赵构南巡,导致东京失守,便是大大的奸臣。
岳飞连战连捷,收复河山,更是千古豪杰;秦桧却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杀害,献媚金国,缔结“绍兴之盟”,难怪被钉死在千古耻辱柱上。
再如虞允文临危不惧,在军队溃败时义不容辞,走上前线鼓励士兵,以少胜多,是有勇有谋,忠义双全。但他赢得采石矶大捷,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后,却再未带兵征战,而是一直待在京城做官,想来自然是没有再为主战呐喊的,不然不会把相位坐得这样安稳。但是谁都不能不承认,虞允文是名臣良相,是爱国志士,也是抗金英雄。
所以韩侂胄罪名不在于北伐,而在于兵败。可是战败是因为内讧,那么真正的罪人应当是谁呢?
韩侂胄北伐失败,宋金签订“嘉定和议”,不但增加了岁币银,而且宋朝皇帝与金朝皇帝的称谓由以前的侄叔改变为侄伯,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
宁宗将耻辱归罪于韩侂胄,下令清洗韩党,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的都被抄家夺职,陆游也以“党韩改节”罪名去职。
打一批,自然要捧一批。于是赵汝愚一派尽复原职,朱熹被赐予文臣最高荣誉的字谥,称为朱文公。一起被平反的还有秦桧,恢复其之前的王爵、谥号。
谁忠谁奸,是不是有点让人凌乱呢?
韩侂胄专政时期的国史记载被修改,史实舆论就这样被扭曲了,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举措称之为“嘉定更化”。
杨万里恨极韩侂胄以至于呕血而死,如果得知韩侂胄死后竟然被割头献金,主张伐金者悉受牵连,秦桧却得以恢复谥号,想必会仰天大笑的吧?
朱熹和杨万里都没能活着看到韩伉胄的结局,陆游看到了。
北伐失败后,陆游极度绝望地在山阴老家度过了余生。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写完那首著名的绝笔诗《示儿》后,溘然长逝。
非特殊说明,本文由诗文选原创或收集发布,欢迎转载
转载请注明本文地址:https://www.shiwenxuan.com/jingdian/202303132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