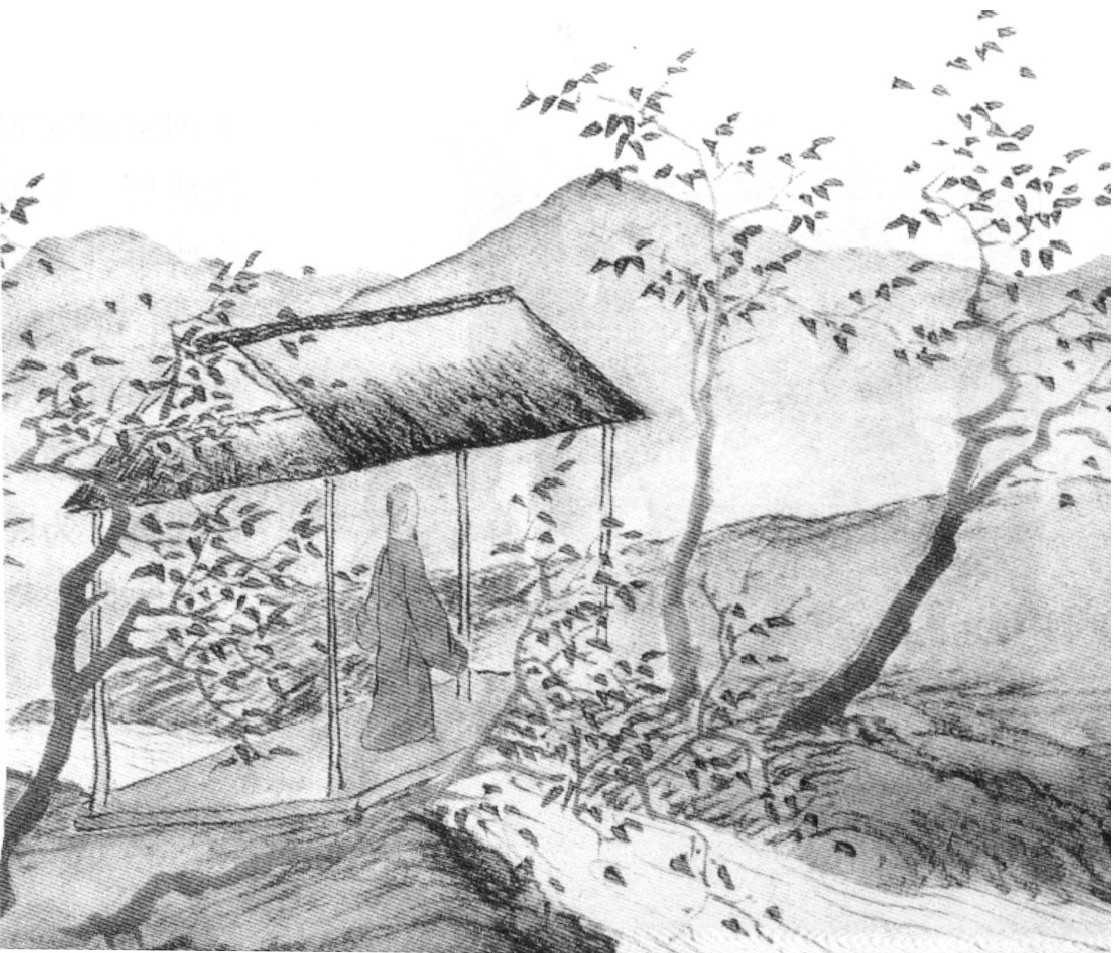朱熹与严蕊:奴非爱风尘,君何贪名气
朱熹与严蕊:奴非爱风尘,君何贪名气
一
我写古人,有些想法是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比如朱熹(1130—1200)。对朱熹的认识,最早是从严蕊的故事开始,所以打小就讨厌这位道学先生;待成长中了解到程朱理学,便更加反感朱熹的虚伪与凉薄;后来重读《论语》,再参看朱熹经注对于孔孟思想的扭曲,尤其是对于科举制度及后代八股的影响,简直恨不得上天从未生此人。
依我说,他就是儒学最大的恶瘤,科举的千古罪人。
正史之前,先说八卦。故事的流行版本是这样的:
浙东常平使朱熹与台州太守唐仲友不睦,六上奏章历数其二十四项罪名,但是有罪名而无证据,因此孝宗迟迟不予理睬,只是将两人俱调离台州,希望他们不要见面也就没了争斗。
可是朱熹向来是辣手判官,说什么都要将唐仲友治罪。贪污腐败什么的一时搜不到实证,就从风化下手。反正朱熹的理学炒作也是先拿女人说事儿的,完全知道怎么做才更能引起百姓注意,主导舆论风向,所以就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直接抓了歌伎严蕊入狱,酷刑拷打,让她招认与唐仲友的“奸情”。
严蕊是天台营的上厅行首,也就是乐伎头牌,色艺双绝,琴棋书画,歌舞管弦,无所不通。
前面说过,按宋朝法制,官府有酒宴,都会召官妓弦歌侑觞,却不能过夜共寝。但是法度归法度,禁不住郎情妾意、男欢女爱,难免有些偷越雷池的行径,人们也多不当一回事儿。比如欧阳修在洛阳为官时与歌伎私会,钱惟演发现后也只是命他即席填首词作罚,对歌伎的失席之罪非但不予惩治,还赏了根簪子助兴,传为佳话。
但是朱熹实在抓不到唐仲友的小辫子了,只得出此下策,拿歌伎说事儿。又或者,朱熹本来就有窥私虐妓的癖好,舍不得放过大好机会,更是嫉妒台州名伎严蕊对唐仲友的垂青,不把两人狠狠羞辱作践一回,不能满足心底的阴私欲望。
于是朱熹再上奏折,专以严蕊说事,说唐仲友每有宴会,严蕊必至。
可是这算什么罪名呢?
唐仲友是官,召伎侍宴非但合理,简直是必然流程。唐仲友唯一的把柄只是偏爱严蕊,每宴必召而已。可是唐仲友又不瞎,他看得见严蕊的美貌,听得见她清婉的歌声,更欣赏她的才情,所以格外看重,这有什么错呢?
但是朱熹非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认为这一男一女既然互相欣赏,必有奸情。他自己是个伪道学,认定天下君子也必然同他一般虚伪,只要拷问就会真相大白。唐仲友是官,不能轻易拘捕;可严蕊是歌伎,是女流,可以肆意欺侮,屈打成招——这就是当世大儒朱熹的如意算盘兼正义招牌。
但是事情再次出乎朱熹的预料了。
居然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女子,居然一个歌伎的骨头会比朱熹这位道学先生更硬,更知道什么是节义和风骨,这太让朱熹抓狂了。
严蕊入狱后,衙吏鞭笞逼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然而严蕊不惧官威,不屈棍棒,无论官府怎么拷打诱供,只坚持说:“唐大人官风清正,与奴之间清清白白,绝无苟和之事。”
威逼不行,那就利诱吧。于是朱熹命人对严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你是官妓,就算真有逾矩,也不是什么大罪,最多就是打几板子算数。如今你挨过的板子早就超过量刑了,就算招认供罪也不会再有任何刑罚了,何必执着,再受皮肉之苦?”
严蕊却坚持说:“我虽为歌伎,亦知义气二字,焉能以白为黑污损士大夫清名?真就是真,假就是假,让我诬蔑唐大人,虽死不能够。”
“义气”——身份卑微的官伎严蕊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可比理学大儒深刻得多了。在狱中关押日久,多次受刑,严蕊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但是名声却越来越响亮。人们都说这是一位风尘奇女子,当真懂义气,有风骨。
于是朱熹为了避嫌,只得把严蕊转到绍兴府,却私令绍兴太守继续严刑逼供。那绍兴太守是朱熹的忠实粉丝,更是假道学伪清高,见严蕊生得标致,罪名十分现成,竟大义凛然地宣布:“有色者必无德。”下手拷打比朱熹更加酷烈,打得严蕊几乎伤残至死。这已经不是莫须有了,这是以美为恶,连强词夺理都算不上,根本就是指鹿为马。
即便如此,严蕊仍是冰心耿耿,傲骨铮铮,坚决不肯对权贵折腰屈从。
朱熹大人一头黑线,剧情的发展完全不按他的设定剧本来,严蕊怎么都不肯照着对白念台词,交上让他满意的口供,世人的风评自然也完全不是他想象那般,对着唐仲友积毁销骨。恰恰相反,审理越久,严蕊的名声越大,朱熹的处境也就越尴尬。
整件事唯一和他想的一样的,就是风化案果然引人注目,朝野上下都在议论这宗桃色公案,居然一直传到了宋孝宗耳朵里。孝宗觉得两位高官拿着一个歌伎狂打笔墨官司实在不成体统,遂命岳飞之子岳霖为刑狱提典,重新审理此案。
岳霖早知严蕊无辜,别说严蕊与唐仲友清白无染,就算两人真有私情,又算得了什么大事?对一件捕风捉影的风化案进行长年累月的审理,本就是浪费公帑的无聊之举,更何况还问不出什么来。整个案子简直就是个笑话。
因此岳霖的提审不过走个过场,问不了几句就决定将严蕊当堂释放,并问其意愿,此后想何以为归?也就是说,你是要回到伎府呢,还是想嫁人?
严蕊当堂填了一首词,婉转致意:
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词说,我生而不幸,沦落风尘,岂是心之所愿?花开花落,飘零浮沉,都是命运的拨弄罢了。如今大人问我去留,我自是想离开。只是去到哪里,自己却也不知道。大人也别问了,只是放我回归山林,还我自由身便是了。我想我的去处,或是山野林泉吧,到那时,我会将簪花绫罗换了山花布裙,还我本来面目。
东君乃司春之神,此处借指主管伎人的地方官吏。所以上阕分明是严蕊对于命运的控诉,却怨而不怒,措辞婉约。
山花插满头,自然是去到山野,荆钗布裙,代指求取自由。同时也是对“不是爱风尘”的照应,这是对自己归宿的祈愿,也是对岳霖的回复,不愿意官府再干涉自己的将来。
词如其人,婉而不媚,风骨清超。尤其想到这还是一个刚刚从狱中带出,久经拷打遍体鳞伤的女子,就更加令人潸然生怜而又肃然起敬。
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词就被深深打动了,更对可怜可敬的严蕊一掬同情泪,从而也就恨透了褊狭狠辣的朱熹。
后来听说,这段故事可能出于杜撰,乃是小说家言,非为正史,不足为凭。比如岳霖根本没当过提典,也不可能审查严蕊案等,让我很失落了一阵子。
不过,少时的我钟情的是风花雪月,既然从这故事中得了一位梅花风骨莲花品性的绝世才女,还听了一首清雅超然的绝妙好词,便已经足够了,至于朱熹与唐仲友谁是谁非,谁又耐烦细究呢?至于谁最终释放了严蕊根本就不重要,编剧把这个角色派给岳霖,或许只是为了提醒读者:严蕊的罪名亦如岳飞,也只是“莫须有”罢了。
只是如今写这《词说宋朝》,不可戏说妄言,既然朱熹与唐仲友都是历史人物,便不得不刨根问底,深究一番了。
二
首先,我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严蕊这个人物到底是否存在。
朱熹和唐仲友都是史上有名的,虽然唐仲友的传记被朱熹后人从《宋史》中剔除了,但是稗官野史中多有记载,不难查其身世。
但是严蕊,人如其名,浮花浪蕊,风尘贱籍,就不易细考了。
南宋时记载这件事最早的笔记小说是辛弃疾好朋友洪迈所写的《夷坚志》,更详细的故事则是隔了几百年的凌濛初写在《二刻拍案惊奇》中的版本。
洪迈与朱熹为同时期人,且和杨万里有私怨,撰文中对朱熹有所褒贬是非常可能的,但若全盘虚构,只怕当时就会被理学门徒的唾沫星子淹死了。他既然敢写,便是实有其事,记录纵有出入,却非空穴来风。
《夷坚志》里明确写道,“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确定了严蕊其人及其才名。并说朱熹将严蕊下狱后,“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
打了五百杖还嫌轻,朱熹这是恨不得把严蕊杖毙,来个死无对证吗?五百杖是不可能一次执刑的,这就难怪严蕊被审了两个多月。
想想看,一个纤纤弱女在两月间连续受刑,前后被杖五百下,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凌辱,这是何等残酷?朱熹莫不是心理变态?
这段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严蕊其人是有的,朱熹设狱刑拘严蕊也是事实。这,已经足够了。
周密的《齐东野语》作于南宋晚期,和朱熹、严蕊已经隔了百年,或不足考,却翔实许多。虽然关于严蕊的生卒年月、身世籍贯仍不可考,却知其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
书中还附录了她的另一首词《如梦令》。起因正是台州太守唐与正(即唐仲友)某次置酒设宴赏桃花,召严蕊前来侍奉,席间命其以红白桃花为题歌咏。
严蕊应声谱成一阕,当席弹唱:
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这首小令词短情深,最宜即席谱唱,且不说其可信度多少,至少合理性很强。
词篇为咏红白桃花,发端偏不说桃花,而只说不是梨花,也不是杏花。这倒有点像那首流行歌所唱:“从Mary到Sunny和Ivory,就是不说你的名字。”
卖尽关子后进入正题,但还是没说什么花,只说颜色红红白白,别具仙姿,超拔群芳。最后笔触一宕,由实到虚,联想发散开去,说起武陵旧事来,问你可记得渔人奇遇,微醺往事?
答案不言自喻,自然就是桃花源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了。只不知,严蕊的桃花源又在何处?
《如梦令》本就是讲求情趣的小令,严蕊这首词轻巧慧黠,意蕴无穷,作为即席之作,自是上品。于是唐仲友大喜,“赏之双缣”。
所谓“一曲清歌一束绫”,寇准早年已有此举,可见唐仲友之赏并不为过。只是赞慕之情溢于言表,难免被有心人看在眼中,传在舌尖,攻于笔下,奏与廷上,当成罪证大做文章了。
难怪当年蒨桃一曲《呈寇公》苦谏“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寇准惊出一头冷汗,从此一改旧习,变出一副朴素勤俭的廉正面孔来,赢得了“无地起楼台相公”的美名。
只可惜寇公虽廉,最终亦未能逃得了丁谓的暗算,到底客死雷州;倒是唐仲友被朱熹六疏弹劾,因得严蕊冰心铁骨相护,终究无碍。
至于严蕊的结局,并没有像寻常传奇中的大团圆结局那样嫁了唐仲友为妾,夫唱妇随从此相守,而是脱籍后嫁了位赵宋宗室,遂得终身结果,安然到老。
联想到严蕊的传世词作还有一首咏七夕的《鹊桥仙》,不禁让人感慨,如果说《如梦令》是她的因,《卜算子》是她的劫,《鹊桥仙》是她的果,那么三首词恰恰写尽她一生:她生就桃花命,只求山花归,如今倒做了桂花伴侣吗?
鹊桥仙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 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三
抛开故事本身的可读性,故事中的三位主角中名气最大的自然是朱熹。
朱熹的最大成就,在于对书院发展的推动。
南宋是书院文化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一百五十多年间先后建立书院四百四十二所,覆盖十一个省。其中朱熹自己创建四所,修复三所,并在四十多所书院中讲过学,被认为是当代的儒学领袖。
乾道三年(1167),朱熹赴岳麓书院讲学,逗留两月,听者云集,“一时舆马之众,饮水池立涸”,别说座位供不应求,就连饮水都成问题了。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一呼百应的大儒,为何要与一个小小歌伎过不去呢?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打击唐仲友。
可他和唐仲友又何来的不共戴天之仇,需要下此辣手呢?
其实,说到底仍是学术之争。
朱熹是“二程”的隔代传人,高举的乃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大旗,而唐仲友则属于永康学派,一向反对朱熹理学。
这就是朱熹视唐为生平死敌的根本原因。
文人们因为学术而争,多半是打口水仗,弄到像朱熹这样要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已经够难看了,更何况还要拿一个歌伎说事儿,就更加有失斯文;最让人不齿的是,风化之事,可以审理不可以强判,严蕊既然矢口否认,朱熹还要继续纠缠已是不智,何况拷打逼供?
正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云:“夫唐宋之时,士大夫宴会,得以官妓承值,征歌侑酒,不以为嫌。故宋之名臣,多有眷怀乐籍,形之歌咏者,风会所趋,贤者不免。仲友于严蕊事之有无,不足深诘。”
对一件莫须有且“不足深诘”的风化案穷追不舍,动用重刑,朱大儒可真是正气凛然!
孝宗皇帝收到了朱熹六道奏章仍不予理睬,就是因为深知朱熹心量狭小,所谓罪名根本就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遂嗤笑:“此秀才争闲气尔!”
秀才争闲气,何其委屈了无辜歌女?
再来说说故事的第三位主人公唐仲友。
唐仲友(1136—1188),字与政,又称悦斋先生,浙江金华人,乃莒国公唐俭第二十一世孙。其父唐尧封官至五品龙图阁朝散大夫,兄唐仲温、唐仲义,皆为进士,是实实在在的钟鼎世家,书香门第。
唐仲友少有才名,二十五岁中进士,之后走入仕途。“上书累万言,言时政甚切。兴利除弊,政声赫然。”(《金华耆旧补》)他为学不拘一隅,忌空言,而更重学以致用。著有《六经解》《帝王经世图谱》《悦斋文集》等,并主持刻书,对于文化典籍的传承保存贡献极大,其中刻书《荀子》人称“宋椠上驷”,赞其“雕镂之精,不在北宋蜀刻之下”,至今在日本尚有藏本,被视为国宝。
也就是说,朱熹做的事(注经),唐仲友也做到了;而唐仲友做的事(刻书),朱熹却远远不如。这让朱熹怎能不恨之入骨?
《宋元学案·悦斋学案》中称:“先生素伉直,既处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学。上自象纬、方舆、礼乐、刑政、军赋、职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经史,参之传记,旁通午贯,极之蚕丝牛毛之细,以求见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后世,可见之施行。”
从这段话可见,唐仲友著书是在被朱熹弹劾失官之后的事。不过两人的抵牾却已可窥根本,实因唐仲友与朱熹一般博学,淹通经史,但理念却不同。
唐仲友呼吁:“不专主一说,苟同一人,隐之于心,稽之于圣经。合者取之,疑者阙之。”
当时朱熹理学居于学潮顶峰,唐仲友号召莘莘学子不专主一说,不苟同一人,显然是和朱熹唱反调。更何况他还说过:“三代治法,悉载于经,灼可见诸行事,后世以空言视之,所以治不如古。”
这个“空言”者何指,当真不言而喻,呼之欲出。对陈亮与朱熹“义利王霸之辨”,唐仲友也是斥责理学一派为空言。
难怪连孝宗都深知内理,乃为“秀才争闲气”。
那么朱熹对唐仲友的指摘到底是不是“空言”,是不是“闲气”呢?
抛开严蕊一事不说,只以贪污论来看一组数据就知道了:
唐仲友知台州是在淳熙七年(1180),四十五岁,正是精明强干的年纪。他在台州修建中津桥,修缮白鹤山灵康庙、台州学宫,显然是位好官。(《林下偶谈》:“唐知台州,大修学,又修贡院,建中津桥,政颇有声。”)
修桥、铺路、建学,自古以来都是德政榜样,唐仲友做的每件事都落在实处,不容抹灭。淳熙九年(1182),唐仲友又拨款给百姓修建桐山桥,但是桥还没建成,就因为朱熹的弹劾被免职离开了。
自此,唐仲友远离政局,开坛讲学,再没有担任过官职。这一选择,正与严蕊的“若得山花插满头”一样,足见其清操为人。
朱熹在奏章里诋毁唐仲友鱼肉百姓,人所共愤。可实际上,台州百姓对这位父母官的爱戴一直延续到他离职之后。因为唐仲友被朱熹诬告以致中途离职,桐山桥的修建失了良好监督,修成没两年就遭到损害。百姓们便又找到唐仲友求助。
唐仲友不但翔实地提出修桥意见,且捐出全部家财二十七万文帮助修桥,占了修桥资金的三分之一。
而唐仲友自己呢,据《金华府志》记载,三年后在他病逝之际,因为家贫,连买墓地的钱都没有。
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鸿儒,廉政爱民的能吏,大公无私的君子,却被朱熹及其徒子徒孙诬蔑成贪赃枉法之人,更毁其平生著作,扼杀民智,恨不得让唐仲友三个字从未在人间存在过。这样的道学,何来正义可言?
幸亏朱熹不是秦始皇,只能秀才争闲气,倘若给了他足够的权力,只怕史上就要再来一次焚书坑儒了。
唐仲友善注经史,但不以诗名。最后,且录其一首咏梅诗见其标格。因诗中有一“蕊”字,让我一厢情愿地且将“此花”作严蕊吧。
蜡梅十五绝和陈天予韵
此花清绝似幽人,苦耐冰霜不爱春。
蜡蕊轻明香万斛,黄姑端的是前身。
四
事有两面,任何一种说辞都只是站在不同立场罢了。严蕊案的由来,亦有人说是反对朱熹者添油加醋捏造了来诽谤名儒的,做不得准。
但是朱熹六奏唐仲友是真,提审严蕊是真,而严蕊拒不招供也是真。
换言之,朱熹与唐仲友,确定是势不两立的敌对方。
关于唐仲友的盖棺论定,虽有朱熹举证的诸多罪名,却始终未有证据,反倒是其政绩赫赫,著述颇多。一个被朱熹举为贪官的人竟然散尽家财为民修桥,死后连墓地都买不起,两人谁是谁非,相信有眼睛的人自有明断。
严蕊案已经确定是冤假错案,唐仲友也显然是位清官。然而为他们罗织罪名的朱熹呢?他对唐仲友与严蕊的构陷只是出于误会,抑或后人诬陷?他本人的风评究竟如何?一生业绩又是怎样呢?
且让史实说话。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累官至焕章阁待制,兼为宋宁宗侍讲,一国帝师,位极人臣。
他的得意风光,用他自己的一首《春日》最能代表: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这首诗表面上说春游泗水,实际上南宋之时,山东已沦为金国属地,朱熹不可能去到泗水踏青,所以这里只是指代孔子讲学的地方,暗喻自己推广理学之盛,门徒众多,万紫千红,天下无人不识朱。
而对于读书治学,他也有一首很著名的诗《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两首诗,清楚照见当世大儒的荣宠无限。
朱熹风光跋扈了一辈子,但是由于庆元二年(1196)监察御史沈继祖的弹劾,最后身败名裂,灰头土脸,晚年过得极不光彩。弹劾罪名除了常见的“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等大帽子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罪名是“为害风教”,即有伤风化,真个请君入瓮。
朱熹的同乡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清楚地记载了朱熹风化罪的具体内容:第一项是他曾带着两个尼姑出游,后来还娶了二尼为妾,就连外出做官时都带在身边;第二项就更加骇人听闻,乃是贾珍与秦可卿式的“爬灰”,因为朱熹反对寡妇改嫁,所以他的儿子死后,媳妇只能留在朱家守寡,守着守着,居然怀孕了,虽然孩子也姓朱,可到底该算是儿子还算是孙子呢?
一边高喊着“存天理灭人欲”,一边纳尼为妾,与子媳不伦,这算是哪门子的道学先生?
朱熹说过:“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朱子语类》)
或许他认为歌伎私属官员是人欲,而他与尼姑、与儿媳则是天理吧?这已经不是州官放火与百姓点灯的区别了,根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怎么说怎么做都行,但是你们只能听我说,什么都不可以做;只要拂了我的意思,就做什么都是错。所以就连他看上人家祖坟的风水,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抢来迁葬自己的父亲,而且还迁了三次。
不要说这些是政敌的捕风捉影,因为当皇帝要对这些罪状进行究查时,你猜怎么着?
根本不需要两位尼妾和儿媳妇学习严蕊那样铁骨冰心证清白,因为根本不等她们入狱,也根本不等狱官审案,朱熹直接就认罪了。
最让人瞠目的是,朱大儒不但对这些罪状供认不讳,还在皇上要治他的罪时,涕泪纵横地上书求情,骂自己“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并保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
到底是一代大儒,骂自己都比别人骂得痛快。但让人凌乱的是,不是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吗?这还没上刑呢,朱熹就什么都认了,哪有半点气节可言?如果把他也像严蕊那样关上两个月,杖五百,还不知要招出多少恶迹罪行呢。
或许,正因为他自己好色贪淫,连尼姑和儿媳妇都不放过,所以才认定天下男儿一般黑,唐仲友守着严蕊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佳人,怎么可能只侍酒不陪寝呢?又因为他自己胆小怕死随风倒,所以也无法想象世上会有严蕊这样的人,竟然面对棍棒酷刑都拒不认罪。人和人,真是不同啊。
或许有人会说,朱熹肯定是被冤枉的。可是,朱熹身为帝师,和皇上的关系比谁都亲近,如果事非属实,他是完全有机会为自己辩驳的。可是他不但认了,而且姿态还极其卑微,可见这些罪状每条都是真的,而且真正的罪案还远远不止这些,唯有赶紧认了才有可能求情,至少保得住脑袋。若是不认,只怕监察御史会一直查下去,越查越深,越抓越多,那么朱熹的罪证还不止挖人祖坟,曝人尸骨这些呢。拖得越久,闹得越大,不如借着皇上给他的老脸,赶紧认罪回乡还可以捂着盖着些。
朱熹的学问肯定是广博的,但是做学问和做人从来都是分不开的。虽然不能以人废文,但是他所讲述的道理如果连他自己都不信都不守,又怎么可能是真正阐述儒家道理?
只是,当事人朱熹都承认“伪学”,开始“深省昨非”了,后世弟子却还学得孜孜不倦,自欺欺人地高谈什么“正心诚意”,何其谬哉?
可惜的是,宋朝统治者需要的正是这种虚伪的道义,以此作为钳制思想的工具。
韩侂胄北伐失败后,宁宗清洗韩党,打击主战派,恢复秦桧、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封号或爵位,重新将理学推到了学术最高位置。
宋宁宗不知是不是遭了天谴,所生九个儿子皆夭折,只得立侄子赵贵和为皇子,赐名赵竑。然而在宁宗临死前,那个一手策划暗杀韩侂胄的幕后元凶史弥远竟然矫诏另立,将支脉较远的宗室之子赵贵诚立为皇子,赐名赵昀,这便是宋理宗。
赵昀(1205—1264)虽为宗室子弟,但是支脉太远,父母早亡,生活境遇只比平民好一点点,如今一步登天,真要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晕了。他知道自己登基名不正言不顺,又没有受过皇室正统教育,迫切需要一种虚伪而愚昧的学说为自己站台,于是选择了空言误世的理学。
理宗之所以被后世称为理宗,就是因为他为理学大开方便之门,不但将朱熹重新包装成儒学大师,颁诏追赠太师、信国公,甚至列入孔庙从祀,成为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者,而且抬出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官学教科书和科举经义的标准答案。
与此同时,则是对王安石新学的彻底否定,完全接受了朱熹对王安石“于学不正”“杂糅佛道”的攻击,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导致北宋亡国的罪魁,以此坚定理学的领导地位。
朱熹的地位达到了空前高峰,竟与先圣孔子并列称为“朱子”。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朱熹是成名了,可他高唱着孔孟之学,却背离了孔子思想“仁”的核心,这种名望又有什么意义呢?
蒙古铁骑以武力灭亡南宋后,对于宋代文明而言是一种逆转。但是他们继续将失去了“仁”而谈“理”的朱子学说扯为遮羞布,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试教材。
再之后的明清两朝中,朱熹的地位被越拔越高,遂彻底成为对民智进行洗脑教育的统治工具。儒学彻底被误导了,四书五经、孔孟思想,被荒谬地扭曲成了“朱熹的孔子思想”(南怀瑾语)。
这一场荒谬,竟然延续了八百年,是为儒学一大哀!
非特殊说明,本文由诗文选原创或收集发布,欢迎转载
转载请注明本文地址:https://www.shiwenxuan.com/jingdian/202303132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