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亦诛,不反亦诛
6.反亦诛,不反亦诛
根据淮南王及其宾客的思想动机、武装实力,结合当时诸侯王的处境,淮南王无论谋反与否,结局都是一样的。
刘安不是政治家,并没有与中央抗衡的意愿。刘安的思想主体是黄老道家,主张“淡泊无为,蹈虚守静”,追求“养生”“全性”。《淮南子·诠言训》告诫人们不要追求富贵权力,“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寄,富贵其寄也”,就是说不追求利益和福分,则避免了祸害,就能长久保有现在的东西,正是老子所谓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刘安也没有谋反的动机,父亲淮南厉王刘长因冤屈而死,固然使他甚为不满,但朝廷也表达了歉意,不仅返还了淮南国的土地,而且追封刘长为淮南王,基本恢复了刘安家族的财产和荣誉。作为补偿,刘长的四个儿子相继封侯,除一子早逝外,其他三子后来又晋封为王,虽然是原有封地的再分配,带有分散实力的考量,但王爵毕竟增加了两个,名义上的待遇也未尝不优厚。
刘安也没有谋反的能力,刘安的武装实力也不足以谋反。景帝时期吴楚七国的叛乱,势头非常猛烈,尚且在三个月内被中央剿灭,吴国煮海为盐、即山铸钱,财力十分富足,尚且不能有所作为,以淮南国的实力,更是难以与中央政府抗衡。淮南国即使拥有武装,也不过是用于日常防备而已,避免被临近的王国突然起事吞灭。
相反地,刘安是仁义政治的施行者。刘安对待百姓的政策是很不错的,《史记》说“行阴德拊循百姓”;宾客劝他举兵起事时,他说“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顾念叔侄之情,不愿给汉武帝带来麻烦;刘安抱怨汉武帝要削除他的封地说“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委屈之情溢于言表。这样一个实行仁义政治的宗室贤王,最终被打上了谋反的烙印,并落得自刎而死的下场,反映了政治的虚伪和残酷。
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实质是朝廷与诸侯国的矛盾。对于分封制的弊端,西汉中央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在汉文帝的时候,贾谊撰《陈政事疏》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指出了诸侯王长大后中央难以控制的忧虑,因而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建议多封诸侯从而削弱每个诸侯的实力,实力弱小就不会萌发叛乱之心,具体方法是“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显然是针对齐、赵、楚等大国,结果是“地制一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通过分散土地削弱实力从而达到上下和谐的局面。晁错也在对策中提到“宜削诸侯事”,于是汉文帝“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应该说淮南国的分而为三,说明中央未尝放松对淮南国的警惕,以推广皇恩的名义削弱了淮南国的实力,那么刘安必然处在监视之下,想进行武装叛变是非常困难的。
汉景帝时,晁错推行削夺王国封地的削藩政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诸侯坐大的危害,认为诸侯反叛已是趋势,迟削不如早削。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开始削夺诸侯封地,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因不满削藩而起兵,提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景帝听从袁盎的计策,希望以牺牲晁错换取各国的退兵,可惜一代才子就这样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然而晁错之死并没有争取到和平,七国见朝廷无能,更加肆无忌惮,吴王刘濞甚至自称东帝分庭抗礼,性质已经是犯上作乱了。景帝终于下定决心出兵镇压,在梁国的坚强抵御和周亚夫的率领下,大破吴楚联军,平定七国之乱。经此一事,中央集权走向巩固,诸侯王的势力也大大地被削弱,除楚国保存、另立新王外,参与战乱的六国皆被废除,其他王国相继被分割为多个小国。诸侯王的统治权也被剥夺,“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为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郞诸官长丞皆损其员”,诸侯国的官员由中央任命,诸侯王丧失了独立性,等同于郡县。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建议说:
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这就是著名的“推恩令”,诸侯子弟都希望能封侯封王,朝廷索性送个顺水人情,根本目的是削弱诸侯国的实力。因此,汉武帝诏称“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如此“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焉”,汉武帝亲自批准诸侯王分割土地给儿子的请求。与此同时,汉武帝加强了犯法而夺爵的惩处,以酎金成色为借口,解除诸侯王封爵106人;通过“左官之律”“附益之法”限制诸侯王豢养宾客,掐断了人才的来源;通过盐铁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等措施,把山海之利收归中央,剥夺了诸侯王的财权。汉武帝的举措,目的是使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希望诸侯王做个富贵闲人、不要无事生非了。从此,汉初诸侯国的“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情况不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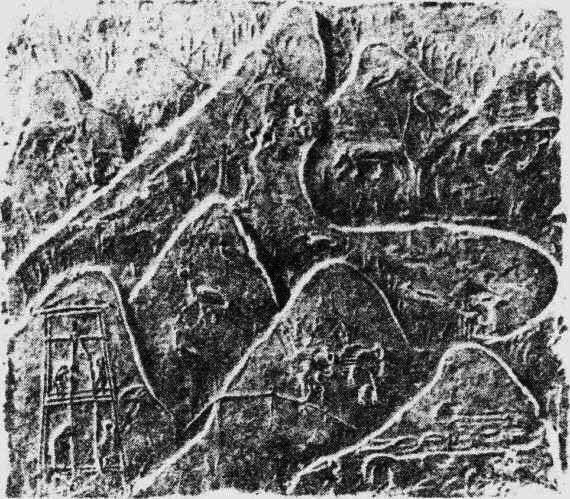
四川出土汉代制盐画像砖
(程征:《纪功的丰碑——西汉霍去病墓及其石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淮南王刘安不知韬光养晦、外示无为,却亲行仁义、爱好读书、风雅自命、啸聚人才、铸成名著,文治的彰显抢了朝廷的风头,自然就成为汉武帝的心腹之患了。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说两汉继承了先秦的游士之风,“诸侯王中若有好学自修之人,则其所集者多在学术上有某种成就之士;于是宾客之所集,常成为某种学术的活动中心,亦为名誉流布之聚中点。这对知识分子及学术的发展而言,常可以发生很大的鼓励作用。但却触犯了专制者的大忌。景帝时代,朝廷猜防的重点在诸侯王的领土和职权。至武帝……猜防的重点特转向到诸侯王的宾客上面,尤其是转向到有学术意义的宾客上面”,淮南王及其宾客志在学术研究上压倒了中央,俨然是西汉一大中心,并且“以其研究充实汉家鸿业的内容”,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武帝表面上尊重叔父,内怀忌毒,左右承旨诬陷,构成其罪,因此“《史记》《汉书》两传中,充满了当时诬构的‘官文书’”,“淮南门客伍被的供词,陈述刘安想谋反的经过,把刘安写成了一个童呆愚稚之辈,其出自严刑逼供,再加以缘饰的情形,甚为昭著”。汉武帝忌惮淮南子的重要方面即是淮南宾客的学术活动,通过对淮南王集团的打击,“不仅摧毁了此一学术中心,并且也阻吓消灭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在生活上一切带有一点选择自由的可能性”,是在儒家思想统治高涨的背景下,收回文化权力、实行文化专制的必然举措。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
同时,淮南王的仇敌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年刘长椎杀了审食其,此举得罪了审氏后人,必然被他们伺机报复。史书说“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审氏后人与丞相公孙弘关系不错,于是公报私仇,不免落井下石添油加醋,铸成冤狱。
我们顺便看看淮南王的弟弟衡山王的谋反案,史书的记载与淮南王案极为相似。《史记》说“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刘安与刘赐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刘赐听说刘安在准备谋反时,也开始准备武器,防止被长兄兼并,当然这些武备后来也被视为谋反的证据;“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刘赐也是方术的爱好者,手下的术士卫庆想攀高枝改投汉武帝,刘赐大怒,通过严刑拷打使其认罪,内史先是不肯,继而应武帝命审理案件,判决刘赐败诉,刘赐又因夺人田地、坏人坟墓被有司治罪,汉武帝不同意,但收回了任官权,刘赐很是不满,因此加紧了谋反的准备;“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六年,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隙,约束反具”,次年衡山王与淮南王见面,冰释前嫌,彼此进行谋反的准备,互相是知情的,这个记载应该是被白嬴揭发的串联谋反的证据。由于刘赐家庭的矛盾,刘赐上书要求废太子刘爽,立刘孝为太子,于是刘爽谴白嬴去长安说刘孝的过错,刘赐担心他揭露谋反之事,先加罪刘爽,刘孝因事自首,于是“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出现了满盘皆输的局面。衡山王之死与淮南王相似,都出于宾客的背叛和家庭的变故,未必有谋反的真凭实据,至于那些武备,无事时可以说防备强盗,有事时也可以说谋反使用,原本就是工具,任凭治狱官尽情发挥了。淮南王和衡山王属于同父兄弟,汉武帝对他们谋反案的发现和处理,终结了淮南厉王刘长一系盘踞东南七十余年的势力。
总之,汉代建朝以来,中央朝廷和诸侯王之间互相猜忌,各自防范,彼此心知肚明。如果说建朝初刘邦处理了异姓诸侯王,是出于稳固刘姓政权的需要,那么吴楚七国之乱,就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在这个教训面前,朝廷加强了对诸侯王的防备,制定了一系列削弱的举措,诸侯王反要被诛,不反也要被诛。诸侯王养士备兵,表面上是防止邻国侵扰、以备异常,实际上枕戈待旦、以示强大,使得朝廷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历史趋势不可逆转,诸侯王不过是在战战兢兢中苟延残喘而已,一旦露出把柄,使朝廷有机可乘,等待他们的必然是覆国亡身。






